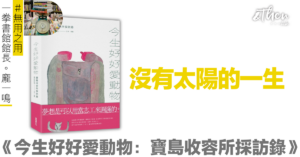紀錄片《毛家》費時四年拍攝,追蹤民間團體「毛守救援」的義工如何拯救流浪動物,無濾鏡地呈現香港浪浪的困境。電影自去年在香港亞洲電影節首映後,現在終於正式公映。身邊不少狗奴、貓奴很想捧場,但「又驚自己睇到喊」。
戲中義工主要救助最乏人問津的老弱傷殘流浪狗,確有心酸畫面。其實人與毛孩都是一條生命,社會總有弱勢基層,慶幸也有好心人。而《毛家》點出癥結:真正的動物保護行動,並非單靠幾位義工救毛孩,而是需要全民教育。催不催淚是其次,觀眾看戲後有多點關注、多點反思,才更重要。
文:凌梓鎏
圖:電影劇照、網上圖片
⚠️注意:以下內容含劇透
義工像在沙漠行走
《毛家》導演區焯文是狗主,拍過關於流浪狗的劇情片《毛俠》(2018),是香港少有的「動保(動物保護)議題電影」。《毛俠》雖小本製作,在動保界不乏迴響,有投資者提議導演拍續集,也有動保義工分享觀後感,指劇情片始終未能反映實況——區焯文有實際體會,例如沒錢弄特技化妝,已無法呈現浪浪的傷勢。於是他把心一橫轉拍紀錄片,展開《毛家》拍攝。
這部紀錄片在2019年至2023年間,追蹤動保團體「毛守救援」(下稱毛守)的拯救日常。由義工收到求助電話、趕往現場救浪浪,繼而安排牠們的醫療、日後的暫托及領養家庭,《毛家》都透過不同個案,讓觀眾了解清楚。浪浪由「無家」到覓得「毛家」,漫漫長路不易走,更未必成功,眼見義工全程同行,隔著大銀幕也感到當中的用心與疲憊。尤其是多個街上救狗場面,義工每每「要幫你,必先捉到你」,即使被蒼蠅蟲蠶食了半邊臉的狗,仍有爆發力狂飆逃跑。有片段見義工多番嘗試,卻捉不到餓扁的瘦弱狗狗,一句「如果今日捉唔到,可能(下次)係收屍」,盡是無力感。


浪浪眾生相是《毛家》主角,而貫穿全片的人物,是拍檔出動的毛守創辦人Kent哥(陸家捷)與義工Jinny。救援總艱辛又閉翳,但兩人的自然互動,為這部「慘戲」帶來唞氣笑位。例如替獲救浪浪改名,是微小的開心時刻(Jinny曾將流浪狗名為「賓治」,因牠下體需要治療);有人將救毛孩的Kent哥叫作「毛先生」,也引來戲院陣陣笑聲。在毛守狗舍,沒人領養的狗隻眾多,醫療費、心理壓力皆是重擔。Kent哥坦言,做救援義工像在沙漠行走,沒水源,走回頭又不是,只能誠惶誠恐地行下去。


毛守創辦人Kent哥(陸家捷)與義工Jinny。
「上面爆屎渠」世界full of shit
很多人看過《毛家》,都難忘Kent哥的「屎渠論」。他說義工如在低層執屎,而流浪動物的問題,其實是「上面爆屎渠」。「上面」即香港整個社會,屎渠一日不修補,再執屎也無法治本。《毛家》的內容,提醒大家浪浪有兩大源頭,其一是天生天養的動物沒絕育,自然繁殖;其二是貓狗因年老、病重、主人要搬家「上樓」等各式各樣的原因,而遭遺棄。
正如導演區焯文曾在影後談,提及動保人士經常引用的甘地名句:「一個國家的道德水平和偉大程度,可用人民對待動物的方式來衡量」。社會風氣與生命教育,是全民的事,Kent哥在戲中也直言,民間組織無法獨力「修屎渠」,動保應由政府推動。回應動保的社會性,《毛家》拍了新界東北發展區的地盤流浪狗,導演形容為「壓軸」部分。其時2022年,發展區內的志記鎅木廠面臨清拆,廠東擔心沒法再餵附近幾隻流浪狗,找Kent哥幫忙。毛守義工要在幾天限期內,嘗試設下天羅地網捕狗救狗,又設置圍欄,又擺水馬陣,人、狗埋身肉搏的場面,相當驚險。


看《毛家》便知,救援行動往往難以100%成功,盡力「救一隻、活一隻」已很好。導演在四年間拍攝超過40隻流浪狗,見證最終僅四隻被領養,毛孩找到好歸宿,展開新生活的片段,也收錄於戲中。對於人也好,動物也好,世界的確像條大屎渠,full of shit⋯⋯但偶爾看見一些生命,會願意救助另一些生命,至少讓我們在屎臭熏天時,仍感到一絲暖意——《毛家》就是這樣的一部戲。此片所有票房收入扣除成本,將全數捐給動物救援機構作慈善用途,又會否成為你入場的理由?




《毛家》
導演:區焯文
片長:103分鐘
上映日期:8月2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