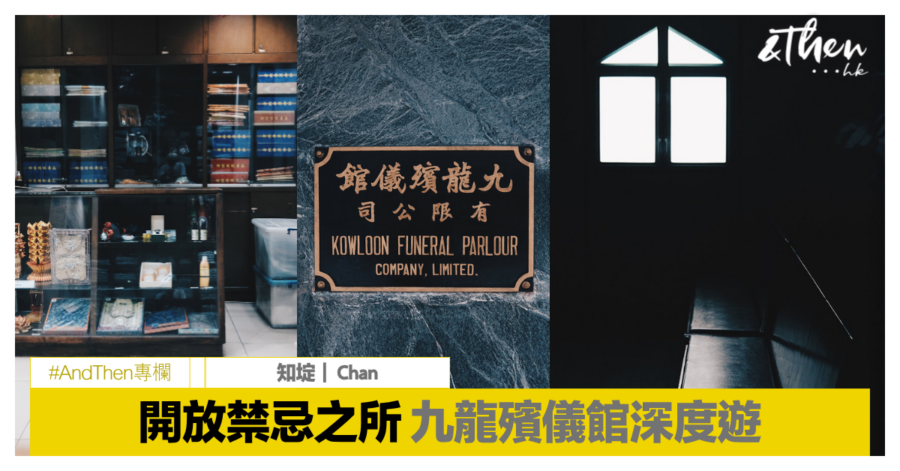幻想一下如此場面:靈堂之內,燈火通明,沒有鮮花與香燭祭品,取而代之是藝術展覽、唱歌表演、手作班、講座分享,熱熱鬧鬧地,沒有人在掉眼淚,有說有笑,在這個平日並不容許「快樂」的場所。
這樣的事,去年的確真實發生過——九龍殯儀館第一次舉辦開放日,吸引過千人報名參加,當時嘉賓率領觀衆在靈堂熱烈地唱《係咁先啦》及《活著VIVA》,於社交媒體引起巨大迴響:殯儀館,可以有幾開放?
近年觀察城市空間的不同個案,往往因為場地的「錯配」運用而覺得極有意思;殯儀館從來不是「學習」與「玩樂」之處,但如果「學」的是生,「玩」的是死,哪𥚃會有比這更為貼切的地方?
今年重陽節,九龍殯儀館再度舉行開放日,把沉重擱下,繼續百無禁忌,坦然地面對生死。

大禮堂將再次成為表演舞台,舉行可容納數百觀衆的音樂會,鼓勵參與者透過歌曲和故事,向故人表達思念。
其他活動包括怎樣預備與家中寵物告別、備受關注的「在家離世」議題,另有建築師到場講解世界各地的殯葬建築及相關文化。
同日亦會舉行破地獄儀式,深入講解傳統背後的慈悲意義,還有遺體穿衣化妝體驗等,節目豐富的程度,基本上就是一次生命教育的嘉年華。
今年比較特別的,是繪本《大耳嘴角》的原畫展覽,繪本作家貓珊的創作,重塑一頭社區狗的故事:「大耳」是九龍殯儀館附屬花店收養的唐狗,於對面大廈出生,由BB開始便以殯儀館的正門為家,一住14年,渡過了一生。

大耳平日在大角咀一帶出沒,極受街坊寵愛,附近幾乎無人不識;2021年不幸被車撞倒後傷重離世,當時九龍殯儀館特地設靈,讓街坊前來悼念,是人人談論的社區大事。
直至今日,大耳走了,卻一直從未離開。殯儀館入口安放著他的靈位,前方是一小顆牛油——那是大耳生前最愛的食物。
路過瞥見的人只覺莫名奇妙,唯獨大角咀鄰里心𥚃明白,牛油溶掉換過新的,一顆接一顆,思念常存。
衣紙灰陶瓷工作坊是另一有趣嘗試,殯儀館與「香港釉藥研究」合作,把祭奠後的衣紙灰回收,製作陶瓷釉藥。

這些來自衣紙灰燼的色調,替陶瓷招福貓披上亮澤外衣,是宗教儀式與工藝的結合,將哀悼轉化為美麗的器物,日常生活𥚃陪伴左右。
開放日點子很多,預計都會引來「破格」、「創新」等形容——而少有被提及的是,那年代九龍殯儀館的出現,本來正正就是破舊立新,為香港殯葬文化打開另一道門,另一種局面。
回到1958年。有「香港殯儀大王」之稱的蕭明和吳海霖(香港演員吳耀漢之父)以77萬元投得大角咀地皮,興建九龍殯儀館,是香港第二間殯儀館,亦是九龍區出現的第一間。

一直覺得,這是一座被傳統習俗「耽誤」了的精彩建築,基於恐懼與忌諱,人們經過一律目光迥避,也許從未清楚看真它的美。
1959年5月落成啟用的九龍殯儀館,至今看上去,依舊莊重得體,單靠線條已能營造出氣勢,低調地顯出份量,經得起時間考驗,早就懂得化繁為簡的好。
背後的設計者,是著名建築師徐敬直,第一代放洋留學的華人建築師,早期曾為香港帶來中西合璧的宗教建築,比如黃竹坑聖神修院、銅鑼灣聖馬利亞堂、土瓜灣聖三一堂,以及赤柱利諾神父會院等。
50年代徐敬直設計過不少現代主義建築,強調實用及以人為本,石澳巴士總站便是其一;九龍殯儀館同樣標榜現代主義的簡潔,相隔幾年後的1963年,美學風格更受稱頌的北角香港殯儀館落成,也是由徐敬直負責設計——如此說來,九龍殯儀館或者會是他小試牛刀的先導?
當時報章形容九龍殯儀館為「設計現代化堪稱遠東第一」;創辦人之一蕭明曾以「豐儉由人」、「待遇無分貧富」作招徠,表示會考慮按需要捐出棺木接濟窮人,這些經手法,無不標誌正規及受法例監管的殯葬服務在民間邁向普及。
可以肯定的是,九龍殯儀館當年由外至內都銳意立新:首先全館室內地方均有空調,並設有自動電梯,予人先進與舒適的觀感,提供優質服務。

此外,它率先聘用女性遺體化裝師,顛覆一貫重男輕女的業界傳統,為後來者奠定重要基石。
至於第三個「新」,至今仍是全港獨有。
走上三樓,迎來一間間安靜優美的小教堂:2008年九龍殯儀館曾經進行翻新,特別將三樓全層改為靜音層,專門為基督教、天主教及無宗教者提供寧靜的追悼空間,方便舉行追思會,自此成為香港唯一擁有治喪用教堂的殯儀館。
借用電影《破·地獄》的對白:「生人都有好多地獄」,現在殯儀館已不單是進行儀式的場所,服務的不獨先人,在生的人其實需要得到更多關顧。
作為城市空間,殯葬設施並不親和,但它的功能可以有更多想像。
開放禁忌之所,讓人走進殯儀館,開明地談論生死,也許會是第一步——懂得如何好好告別,便能擁抱告別前的每一個當下。

九龍殯儀館重陽開放日
日期:10月29日(星期三)
時間:10am-5pm
地點:大角咀楓樹街1號A
報名:於官方網站www.riphk.com登記(部分活動需收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