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:黃子翔
攝影:林志華
如果踢躂舞鞋,踏在地板上發出的聲音,不是「踢踢」和「躂躂」,而是琴音、鼓聲,那算不算是踢躂舞?還是一種超越?本地踢躂舞團STEP OUT Studios,於11月帶來首個電子踢躂舞蹈劇場《The Next Movement》,舞團創辦人及舞者Zoe Chan及CAL,夥拍團隊研發電子踢躂舞鞋多時,終有成果,將在演出裏,訴說踢躂舞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

探索不同可能性
訪問期間,請他們即場示範,CAL穿上電子舞鞋,連接失敗又成功,踢踢踏踏,有時發出爵士鼓的鈸、筒鼓、小筒等聲音,也有「Misfire」的時候。「這是我們這兩年來不停面對的事情。」Zoe苦笑說:「我們都是比較低技術的人,因為這個計劃,接觸了電子音樂,學習相關應用程式,那完全是另一種語言。是有挫敗感,但又覺得很有趣。」她又說,這兩年來,鋼琴聲、鼓聲,甚至怪聲都試過,即將舉行的演出,還有火車聲、玻璃碎聲,「甚至是說話的聲音!」


電子踢躂舞鞋的概念,始自疫情時,大夥兒躲在室內,無得練舞,而在木地板上跳,不僅刮損地板,還吵到鄰居。他們思前想後,有沒有一種踢躂舞鞋,「只得特定的人聽到聲音?」傳統踢躂舞鞋藏有金屬片,與木板碰撞時,發出充滿節奏的敲擊聲音,較跟爵士樂搭配,「但我們想跳出框限。」事實上,回顧踢躂舞的歷史,不少大師都在探索踢躂舞的可能性,譬如試試搖滾樂、Hip-Hop、Rap等等;電影《Tap》(1989年)最後一幕,美國踢躂舞大師Gregory Hines,穿上一對電鞋,舞動時,發出一些電子聲音,「這個概念,許多年前已經有人想過。」
他們便跟樂器設計師及聲音藝術家吳澤霖商量,研究把舞鞋電子化。吳澤霖曾為黃靖2021年結合現場音樂、踢躂舞、編作劇場的《我們在此漂流》,把Converse鞋研發成踢躂舞鞋,跟那場演出的踢躂舞指導及演員CAL結緣,對踢躂舞鞋的鞋底構造、如何影響聲音,已有概念,這次CAL向他提出合作,邀他擔任技術總監,一拍即合,「如果舞鞋沒有金屬片,既不會損耗木地板,又不會吵到別人,通過電腦程式,產出其他聲音,也可以玩其他音樂,可能性或許更大。」
反轉了的Drum Pad
他們也邀請電子音樂人、第三十二屆台灣金曲獎「演奏類最佳專輯製作人」得主hirsk,加入團隊,扛起音樂總監之職。hirsk一直熱衷於探索不同樂器,以至不同作曲、演出方法,這個計劃應該正對口味,但他一開始卻有保留,「這幾年間,有很多Art Tech、新樂器的演出,我有時覺得更像Gimmick,或者讓一些不太想練樂器的人,用一些噱頭的方法,按個鍵就能彈結他。」但他後來跟團隊見面,發現大家想法一致,不是要「Wow Factor」、變魔術,更強調藝術性、實驗性,「大家都很認真,壓力不少,這兩年是漫長的旅程。」


問到電子舞鞋的原理,hirsk解釋,就像MIDI的Controller發送MIDI Note一樣,當感應器感受到壓力時,也會發出一個Note,「跟按鍵或按Controller,沒有很大差異,分別只是穿在腳上而已。」但以雙腳「奏樂」,其實沒那麼簡單,「他們的想法,那就像一個反轉了的Drum Pad,以腳打鼓,但因為牽涉壓力,便有很多複雜的問題,好像地心吸力、人的重量,還有跳高、着地、行走,不只是一下撞擊,很多動作都成了觸發點,衍生很多沒有想過會有的聲音。我們通過不斷測試,作出不少改動。」他也像收集特定數據,然後轉化成聲音或音樂。
每個電子舞鞋的底部,都藏了七個感應器,分別是前方三個,中間一個,後方三個,也就是踢躂舞步法經常用到的七個位置。左右兩腳,一共十四個音,可以「彈琴」?「其實不太可行,腳掌和手指是兩回事。」Zoe接着說:「我們試過彈『生日歌』,不是不可以,但動作會變得怪怪的。」團隊花了超過一年半的時間研發,終在去年年尾至今年年初,製造了第一個樣板,後來又改良到第二至三個版本,到了現在,他們已有專屬的電子舞鞋,根據各自的重量、角度等不同參數調校。
混合新舊步法
他們早前遠赴美國洛杉磯,參與NAMM音樂器材展,並與紐約及國際知名踢躂舞者交流,就像一趟尋根之旅。CAL說:「我們拿着新設計,請示一些踢躂舞大師,覺得有某種使命感。」他們拜訪的踢躂舞者,包括Lisa La Touche、Nicholas Young、Warren Craft等等,請他們試穿電子舞鞋,收集意見,回港後進一步改良,「他們的意見,有八、九成都很正面,覺得有趣,就連鼓聲、琴聲都可以做出來,敞開踢躂舞者的創意。」各人穿上電子踢躂舞鞋,立即探索這對鞋如何運作,「因為底部有感應器,不同位置觸發不同聲音,影響舞步動作。」

電子舞鞋和傳統舞鞋的舞步動作,不盡相同,Zoe覺得,有種拋棄所學、重新學習的感覺,「一開始的確覺得跟踢躂舞相距甚遠,便漸漸放下踢躂舞的概念,重新學習怎樣以電子舞鞋跳舞,但跳着跳着,又找到共通點。也因為電子舞鞋讓我們有了新步法,跟傳統步法混合起來。」他們就是想作出挑戰,「我們已跳了傳統踢躂舞一段時間,在創作上,有時會有樽頸位,也不想只是娛樂大家,希望給觀眾傳遞一些訊息。」當聲音、視覺改變了,「能否講更多故事?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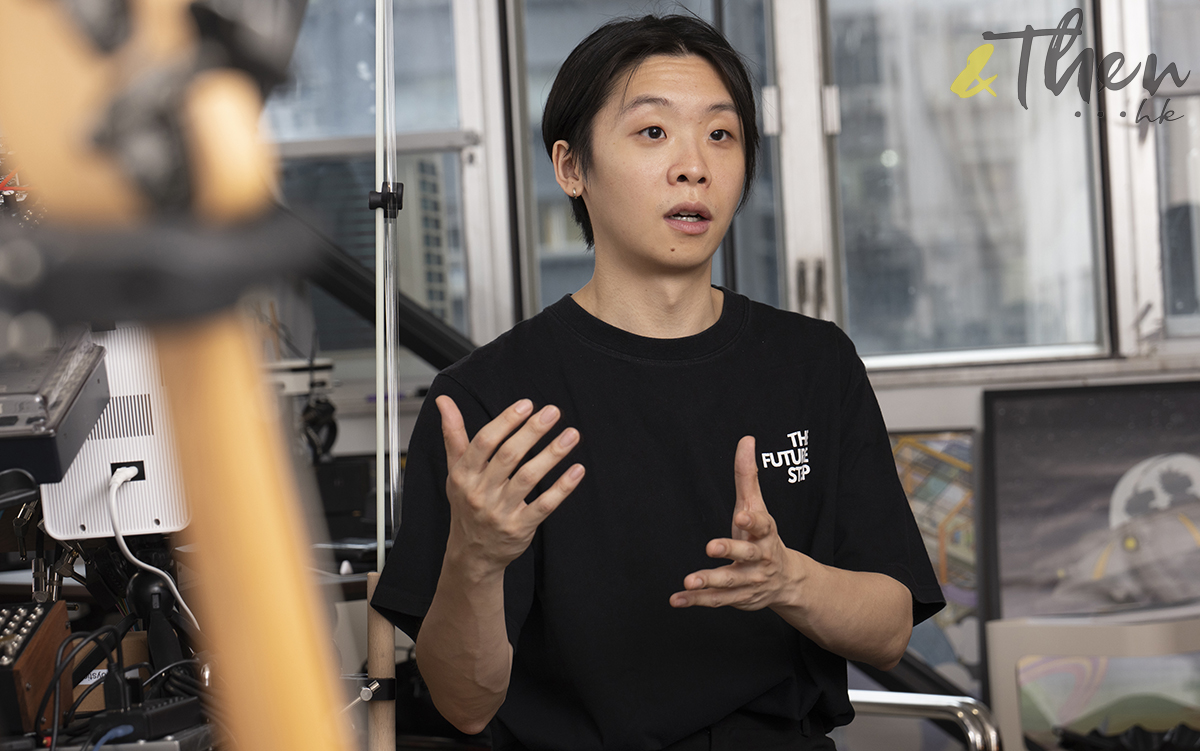
走到哪裏 跳到哪裏
《The Next Movement》演出約九十分鐘,是一個舞蹈和音樂元素較重的劇場作品。曾奪第二十八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王俊豪,為是次演出執導及劇場構作,他說:「他們跳踢躂舞、作為藝術家的經驗,如何走得更遠?怎樣突破?就像一個探索的故事,有敘事性,但不是話劇那種形式。」這兩年來研發電子踢躂舞鞋的過程,起起跌跌,自我懷疑,遇到限制,尋求突破,「探索踢躂舞的未來,是演出的核心。」


五位舞者,有時獨舞、雙人舞,有時群舞,hirsk說:「就像合唱,為他們分配不同聲部。」演出還有影像投影、燈光設計,王俊豪說:「電子舞鞋可以觸發影像和燈光的變化,好像開燈關燈、改變顏色,是新樂器、感應器、控制器。」也有現場音樂,除了即興Jam歌,還以舞者動作「作曲」,「電子舞鞋似乎可以取代現場樂手,但如果有樂手參與,跟這對鞋發出的音樂,會是怎麼樣的組合?」Zoe說:「當我們成了『樂手』,怎樣跟現場樂手共存?一個用腳玩的鼓手,跟一個用手玩的鼓手,迸發甚麼火花?」是碰撞、對話,也是溝通。

穿上一雙電子踢躂舞鞋,還可以走多遠?「如果感應器,成了即裝即拆的一塊,黏在哪雙鞋子都可以,然後連接應用程式,接駁耳機、揚聲器,不就可以走到哪裏跳到哪裏?」下一步,繼續Think Big。
《The Next Movement》
日期及時間:11月21日及22日 8pm|11月23日 3pm
地點: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購票:www.art-mate.net/doc/87879
IG:www.instagram.com/stepoutstudios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