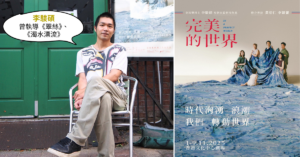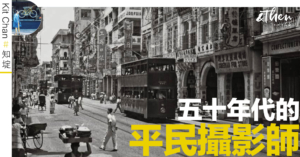黎濟銘和陳琬瑜(Caro),是電視劇《哪一天我們會紅》的西瓜先生和修女,也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《月明星稀》的阿明和太初,一個是因為工作關係跟妻母分隔兩地的科學家,一個是敢作敢為的漂流女生,各懷心事;他們演出優異,分別獲得及入圍「IATC(HK)劇評人獎」2024年度演員獎,受到好評。《月明星稀2.0》演出在即,兩個角色均有修訂,經歷一年的累積和沉澱,他們已作好準備,決心交出更佳演繹。
文:黃子翔
攝:林志華
圖:前進進戲劇工作坊


Detach、Attach再Detach
《月明星稀》講離別、去留、重逢。對於近年跟很多朋友說再見,阿銘直言不快樂,「其實對自己的生活沒太大影響,那些朋友也只是一年見四、五次,但不知怎的,就是不快樂。」他想過離開,曾下載BNO應用程式,填好資料,「有一刻甚至覺得不是一時衝動,而是很想離開,重新開始。」最後還是工作讓他留下來,「也想通了,是某種想法上的妥協。先專心做好想做的事吧。」
Caro的爸爸是香港人,媽媽是西非人,她在香港成長,有強烈的香港人身份認同,儘管看起來不像,跟別人說自己是香港人時,得到太多懷疑和否定,「這件事不會完,我要一直面對。」對於移民,她覺得很正常,不局限於某個年代,沒有好壞,只是現實,「爺爺在二戰時從廣州來到香港工作,然後結婚,落地生根。從事電子工程的爸爸,曾在不同地方謀生,於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,到了不少華人在當地設廠的西非,認識了我的媽媽,後來她從西非嫁到香港。」因為多元文化身份,她對於離散、去留,自然而然產生免疫,「已習慣讓自己Detach、Attach,再Detach。做演員亦然,進入一個角色,然後離開。」是Reality,「Always Checking。」


跟阿明的靈魂碰撞
2016年畢業的阿銘,坦言獲獎讓他得到很大鼓勵,不只在《月明星稀》的表現獲得認同,「更像總結了我在這個行業的經驗累積,一直以來做的事情沒有白費,有人看得見。」跟阿明的距離?「很遠啊,他是社會上的精英份子,很聰明,也有自己的家庭,我不是這樣的人,身邊也沒有這樣的朋友。」
但阿銘最初接到劇本,讀着讀着,瘋狂地哭,那是靈魂的碰撞,「雖然阿明是一個科學家,同時也是一個敏感的人,在心底裏收起了很多沒有處理的情感和經歷,只是壓抑下來,但一直纏擾他,甚至影響他不少決定,當看到某些畫面,便重新面對那些抑壓。」這種狀態,讓他跟他,相連起來,「我們在感性上很接近。」他估計自己與阿明年紀相若,事業發展的狀況,也有相似之處,「三十多歲的男性,在社會上怎樣走下去?」很多事情,不是說有就有,面對其他機會,要還是不要?他把自己現階段在事業上的迷惘和感受,「借給阿明用。」

阿明在西班牙赫羅納工作,實驗室就是他的世界,雖然推開大門,外面是不一樣的語言和文化,但無論身處何方,他的世界似乎沒有變改,「理論上他可以不問世事,但儘管沒有主動接觸,異地文化還是會『找』他,逼他去看去想。」阿銘最長只在外地待上兩個月,坦言不太體會在外地生活和工作的感受,「但旅遊時受到的文化衝擊,怎樣面對、適應一個新的文化,以至因而產生的身份認同,都能應用到阿明身上。」
「外來者」與太初
在演藝畢業後,Caro便去試鏡,順利得到《月明星稀》太初這個角色,「這套戲,陪了我兩年,可說是看着我成長。」她沒想過會入圍獎項,還跟蘇玉華、葛民輝等資深演員一起競逐,最初甚至病態地把入圍名單看了又看,「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名字!」既是壓力也是動力,現在多了一次演出機會,「要做得更好!」一直以來,她覺得自己跟其他人很不同,不知能否繼續在這裏發展?觀眾是否想看自己做戲?入圍獎項,就像給了自己答案:「繼續走下去!」
原來編劇陳炳釗寫劇本時,曾訪問她,然後把她一些經歷放進角色裏,「但太初畢竟是虛構人物,到底我是演『自己』,還是通過一個距離,想像太初這個角色?只是做自己是不夠的,希望可以扣連得更好。」她曾跟阿釗談及自己的看法,「他很願意聆聽,然後修改。」在香港成長的她,十九歲起旅居台灣五年,期間修讀英國文學,「在成長過程中,大家覺得我是一個『外來者』,便試試離開香港,做一個真正的『外來者』。」後來演藝收了她,她又回來了,「花了頗長時間,跟香港重新連繫,包括語境、朋友、家人。」她的姐姐以至一些朋友,已離開香港,加上疫情,「這是我最能連繫太初的狀態。」

太初在德國開咖啡店那一段,她花了不少時間想像和研究,「雖然我也當過侍應,懂得沖咖啡,但沒去過德國,更對當地的Freelancer簽證,一無所知。」太初這個角色,也牽涉其他種族,如巴勒斯坦,她向朋友請教,發掘更多素材,「惡補」國際視野和文化,「還有太初的朋友Genesis,是LGBTQ社群,我也做了功課,研究怎樣處理和呈現大家的相處。」還有太初好友阿遠,「我本來不認識鍾益秀(飾演阿遠),但太初跟阿遠是一對很好很好的朋友,雖然我看起來很開朗熱情,但還是要時間與人混熟。」她們在戲中有擁抱的情節,最初排戲,難免尷尬,「後來變得很自然了。」無論劇場內外,她們都有互動,發展出屬於她們的化學作用,「去年她邀請我,參與她在麥當勞辦的生日派對!」
從省略號到句號
《月明星稀2.0》新版再演,不同角色有了不同修訂,同時衍生一些新情節。Caro之前覺得太初很天真,甚麼計劃都沒有,便不顧一切去外國找朋友,但朋友都離開了,自己還是繼續留下來,「為甚麼那麼『傻豬』?現在反而會欣賞她這種純粹,想做就做。」新版的太初,似乎有了預知能力,但她笑說那不是甚麼超能力,而是對要怎樣做多了一種感知。她很羨慕太初那麼敢作敢為,「要100%相信,很難啊!」

阿銘覺得,首演時阿明那條線的結局,是一個省略號,只是環境逼着他去適應,最後跟太太去了英國,但沒有處理他的心理困惑,「編劇在新版則為阿明寫了一個句號,令這個角色的輪廓更鮮明,觀眾會看到阿明到底卡着甚麼,也多了一場跟太太對話的戲,他們的關係更清晰,故事更圓滿。」
從讀劇、首演到重演,歷時兩年,香港這兩年間也有變化,「去年大家對於離散,仍有很多問題和不確定,今年大家的看法已有不同,我也沒那麼迷惘,面對移民的困擾少了,我會說豁然開朗,相信或多或少也會投射到演出裏。觀眾同樣經歷社會變化,再次進場,說不定有新啟發。」演員、觀眾都Move on了,但角色沒有,在劇場裏重複着那些生活,「一年後,我們再次面對這些角色,有甚麼衝擊?」

致演員
Caro最近在讀契訶夫的《致演員》,「這兩年來,好像有很多機會。你看社交媒體,每天都有洗版式資訊和娛樂,作為演員,可能會怪自己,為甚麼不更主動爭取、出擊、經營?我開始質疑做演員這件事,甚至想過逼自己做一些內容,或者用『修女』這個角色拍片?」但《致演員》提醒她演員的基本,「看劇本、研究角色,不如先集中這些吧,其他事情,喜歡才做,不要逼自己了。」

阿銘也認同現在的確有更多機會,甚麼都可以拍一下,但自己喜歡、適合自己的工作,未必多了,「看到媒體這個大海,更清楚自己作為演員的定位。某些YouTubers、內容創作者所做的事情,我不會理解為演員工作。的確需要經營,但不是要經營一個藝人的形象,我想保留自己能演不同角色的可能性。」他將於8月演出獨腳戲《冚家拆》,笑說來到這個階段,很想挑戰自己的演員能力,「一個人擔起一個故事,需要很多創意和技巧。也是時候測試自己的人氣!」他去年面對收地的事情,找到很多資料,覺得可以成為獨腳戲素材,以自己的遭遇,連繫家族歷史和社會狀態,「捉到鹿,看看能否脫到角?」後續在即,他們自己大概也迎來2.0、3.0,還有更多變化。

《月明星稀2.0》
日期:7月12日至20日
地點: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
購票:https://www.popticket.hk/event/flowing-warblers-2
https://www.art-mate.net/doc/82801